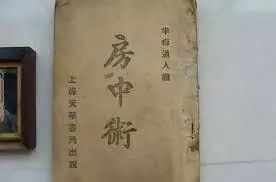
自德国科学家克拉夫特•埃宾在1886年发表《性心理病》一书,被国际上普遍认为是现代性学奠基之作。算起至今还不到两个世纪,而在我国最早研究男女闺房性生活的时间,可以上溯到殷周之际,因此可以说,我国古代房中术实际上是全世界各民族中,研究得最早最深的性科学。对于发展今天的性医学、性保健、优生学乃至老年医学来说,都将有很大裨益的。
古人认为:“房中之事,能杀人、能生人”,就象水能载舟,水亦能覆舟一样,这是很有道理的。晋代医学家葛洪指出人不可以阴阳不交,坐致疾患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认为:“男不可无女,女不可无男,无女则意动,意动则神劳,神劳则损寿”。据《史记•仓公传》所述,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,不时发寒热,淳于意诊脉所说,内寒,月事不下,此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。清代诗人袁枚在《小仓山房文集》里记有名医徐灵胎案例,谈到商人汪令闻因长期不过性生活而得病,徐氏诊断后并不开处方药,只劝说汪氏回家与妻子同居而愈。
何为房中术房中术,来源于古代巫觋,又名道教黄赤之道,玄素之道。房中术依托黄帝、素女、采女、彭祖、龚子、容成公、三张施行此术,所谓“黄老赤篆,以修长生’陶洪景《真诰》称为黄赤之道。房中术本是讲房中禁忌及却病之术,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:“乐而有节,则和平寿考,及迷者费顾,以生宗而损性命”。道教重养生之道,也主张广嗣,所以道教倡导此术。认为可以爱精气,求得“还精补脑”,至于后来误解为猥亵之术,乃妖妄欺诳。北魏寇谦之曾反对“男女合气之术”,他说:“大道清虚,岂有斯事!”晋葛洪也说:“单行房中不能致神仙,也不能去祸致福。后世道教信徒中,也没有房中术的流派,道教全真派系出家道士,主张禁欲,更是反对此术。
房中术又名“房术”、“房中”、“房内”、“黄赤之术”、“男女合气之术”,是中国古代医家和道家关于如何在男女性生活中获得乐趣、保健、胎教、优生、延年益寿的学问。
基于道家的阴阳思想,把性作为一种修身养生的方法。房中术的这一性质,在历史上更多的被人用作淫秽之术,因此也经常遭到政府的封禁,其本身的内容反而被大多数人不了解。房中术有三等:上者,利己利人。
中者,互有损益。
下者,损人利己,魔道之行
道教之外,一般认为房室之事是有损无益的,如果不是为了人伦和生理的需要,而仅为享受那是要付出代价的,所谓“一滴精一滴血”,每一次性生活都是对生命的损耗。唯独道教,既适嗜欲于世俗之间,行不离世,举不观俗,又善于从世俗生活中寻求探觅适合实现其宗教目标的途径。在道教中认为,房中之事不但无损,而且有益,只要行之有法,操之有术,就能采阴气而补阳气,“却走马以补脑”,达到长生不老的效果。
房中术的本旨是调协阴阳以养生,有着合理核心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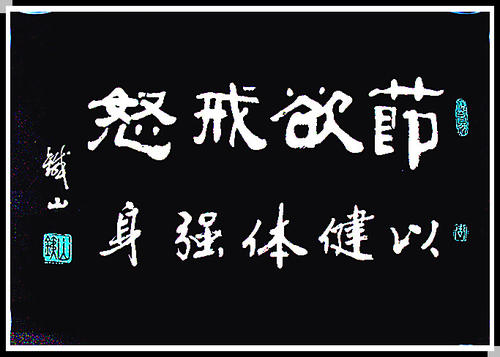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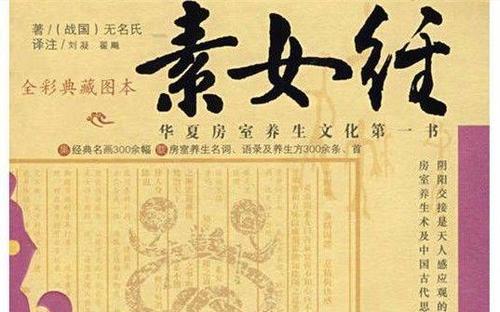
道士刘京提出:春三日一施精,夏及秋一月再施精(两次),冬常闭精勿施。《素女方》和《玉房秘诀》还提出日月晦朔、雷电风雨、饱食后、体疲劳,及大汗未干等不宜房事之七忌。据说彭祖加以归纳为三大忌:大寒、大热、大风、大雨、大雪、日月蚀、地震、雷鸣等自然变化强烈时,天忌醉饱、喜怒、忧愁、悲哀、恐惧、疲劳、远行初归、金疮未愈、女子月事未绝、忍小便交接等,为人忌;神庙、寺观、井灶等处为地忌。诸书并对违犯上列禁忌之恶果作了详细说明。
《素女方》谓,日月晦朔时合阴阳,“令人临敌不战,小便赤黄”;雷电风雨时合阴阳,“生子令狂癫,或有聋盲痦痖”;饱食后合阴阳“六腑损伤,腰脊疼痛”。
02男子六错一忌三元节。庚申甲子伏腊,本命元辰,朔望弦晦。
二忌作干劳困。气力奔冲,远行无力,才下车马。
三忌连日饮酒。久病初安,元气未完,然怒惊恐。
四忌言语过多。交接频数,行早卧迟,观玩劳倦。
五忌神庙、迅雷、烈风、日月星辰之下。
六忌大寒打颤、大热汗流,大饱伤心损气,大饥大醉,无力主张,心中好欲,久淫不止,津闭不出。
以上皆不宜交欢,静而守之。须择日,必阳上半日,阴下半日,甲日为阳,乙日为阴,余仿此。专忌子前,乃阳生阴盛之时。凡交须饮酒一二杯,或茶一盏。恳晚饭夜食。使气脉流通,精神清爽,然后两意相孚,战不衰矣。纵观古代名家之言,七少认为:”房中书“,不是追求的奇技淫巧的荒淫之术,而是为求天道阴阳相和,延年益寿,其中种种不便细语。以上所说,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。